2015年04月01日11:34 來源:上海文學 作者:于建明 點擊: 1398 次
【編者按】著名作家、原上海作協副主席、《萌芽》雜志主編趙長天同志于2013年3月31日逝世,今日是兩周年祭日,特轉發于建明發表于《上海文學》2015年第三期的文章《無形的碑——追憶趙長天》,予以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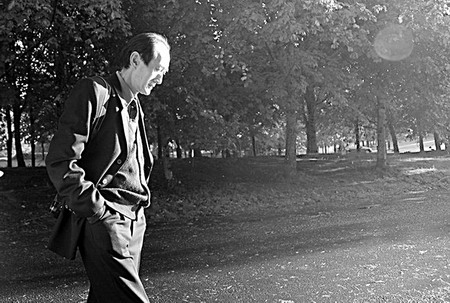
無形的碑——追憶趙長天
文/于建明
1982年12月底,我從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隊轉業到上海航天局宣傳處工作。報到的那一天,宣傳處長老張向我介紹處里的同志,輪到趙長天,特別加了一句:小趙還是作家。我們緊緊握手,不是禮節性的,能感覺得到他的熱情和真誠。他笑著說:“我也當過兵,上個月剛調到處里來,前后腳,我們都是新兵。”一句話就化解了我的拘謹和緊張。在部隊里,新兵見老兵,要立正,要敬禮,就像新媳婦見公婆,矮一截,要熬。初來乍到,心里沒底,有他幫我一塊兒墊底,我心就定了,對他有了親切感。
那時的長天,人很瘦,個高,皮膚白皙,天庭飽滿,雙眼炯炯有神,身著深藏青色呢中山裝,藍軍褲,三接頭式皮鞋,精氣神十足。這是我最初對長天的記憶,深深的、揮之不去。盡管隨著歲月的流逝,看著長天皺紋爬上額頭,開始掉發了,謝頂了,落牙了,后又患了牙周炎,牙全拔了,裝了整整齊齊的假牙,白白的,也挺好看。他寫過一篇《牙祭》的短文,不過癮,又寫了《牙祭》續篇。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表達了中年人的一種復雜、無奈和豁達的心境。他年紀長我幾歲,可能是天天上班在一起的緣故,相互看順眼了,仍然覺得還挺年輕。他堅持游泳,鍛煉身體,外出開會、參加活動,帶上游泳褲,條件允許,就會下水不停歇地游上半個多小時。只要身體好,會來日方長。
直到在那多結婚的那天晚上,長天從醫院請假來到兒子的婚禮現場,他和夫人相伴著,滿面笑容走到我們作協朋友的桌邊,抱拳致謝,不停地說,謝謝,謝謝。婚禮場面很隆重,很熱鬧。我遠遠看著長天夫婦站在典禮臺上,為容光煥發的兒子祝福,內心很是感動。我們熱烈鼓掌,為那多祝福,也為長天祝福。
婚禮儀式圓滿結束后,長天又走到我們這些老友身邊,他再次抱拳致謝并告別,有些戀戀不舍。有段時間沒見到長天了,心里惦記著,但又不便經常去看他,打擾他,想讓他靜心養病,期待他能早日病愈出院,繼續共事。看著他白發蒼蒼、消瘦蒼老的臉龐,和轉身緩緩離場的背影,我內心一陣凄涼,鼻子酸酸的,眼水在眼眶里打轉。
盡管那是個喜慶的場面,那多要為父親盡孝,想為父親沖喜。長天很疼愛兒子,但流露出來的疼愛方式和常人不一樣。記得那多小的時候,局里舉辦文娛活動,長天就會帶他來玩。他很調皮,大樓里到處跑。長天不太管,最多說一句,輕一點兒。有時另一位同事也帶兒子來,年齡要比那多大一點,就讓他們下象棋玩。那位同事老是站在旁邊看,關鍵時刻,還要幫兒子指點一下。那多下棋很認真,有時會抬頭掃一眼長天,但好像不太理會和計較輸贏。長天遠遠坐在辦公室的另一角看著,偶爾會沖兒子笑笑,很隨意、很溫馨。我們有時聊天,長天說到兒子小時候很頑皮,老師要告狀,讓他們操心的事,口氣很輕松,好像不太在意。但有兩件事他講起來卻津津有味:一件是,家里清理廢舊報刊雜志要當廢紙賣,兒子卻悄悄拎到小區路口擺地攤,一本本賣。另一件是,兒子在海關學校讀書時,在一次班會上大談金庸、古龍和武俠小說,把同學們和老師說得目瞪口呆,鎮住了。兒子很興奮很得意,人開始有了重大變化。長天說,這是刻意教不來學不會的事。如今兒子長大,子承父業,又完成婚姻大事,懂得關心體貼父母,長天應該放心了。那天,長天西裝革履,顯得很高興,但我真的感到了他無可挽救的衰老。
1980年代的上海航天局坐落在外灘15號大樓。20世紀初建造,最早是華俄道勝銀行大樓。1990年代,被置換成上海外匯交易中心。那時宣傳處的辦公室在三樓朝東,隔著中山東一路就是黃浦江。中午休息的時候,我和長天常站在窗前,一邊聊天,一邊眺望著黃浦江上穿梭往來的船只。海關大樓的鐘聲定時在耳邊敲響,深沉而悠遠。
長天1968年參軍,是大涼山上的空軍雷達兵,和我一樣曾當過副指導員,后被調到“空成指文工團”任創作員。1976年復員回滬。那時部隊干部轉業要等指標,復員不用,但選擇復員就意味著前功盡棄,放棄干部編制,放棄金飯碗。長天說,那時他父親重病纏身,母親身體也不好,需要照顧,他要盡孝。他還說,他姐姐叫秋水,名字是父親從唐代王勃的《滕王閣序》中選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他有一位才智情商很高的父親,他很得意。
回滬后,他進了上海有線電廠,從工人做起,以后重新轉干,當過車間主任、支部書記和宣傳科長等,后被調局宣傳處當干事,提副處長。那時,他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發表過不少小說,還得過獎,也屬于青年干部培養對象,很受同事們的尊重,但他始終保持平常心,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上班早到辦公室,就忙著擦桌掃地泡開水,里里外外忙上一陣。
在宣傳處我兼管圖書采購工作。除了選購宣傳工作需要的政工類學習參考書籍資料外,很想再買一些經典的文學類書籍,但又擔心有人會說閑話。我與長天商量,他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看些文學類的書,這也是務正業,有意無害,沒什么問題,我陪你一起去。”于是乘中午休息,我們常去逛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商量選購書籍,他幫我一起興沖沖拎回辦公室。單位離書店不算遠,走快點兒十來分鐘就能到。為了多擠點時間逛書店,又不耽誤下午上班,有時中午不去機關食堂排隊吃飯,路上隨便買個面包墊一下——我知道他是用行動在支持我。
我們都喜愛文學,又都當過兵,情趣相投。我曾寫過評論他的文章,他很愿意跟我談論文學話題。他有了創作想法,常會找我聊,就是講故事,聽意見和建議,我們也是文友。那時期創作的《市委書記的家事》、《老街盡頭》、《天門》、《蒼穹下》和《冬天在一座山上》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珈藍夢》等,已充分顯示出他很高的思想、文化和藝術素養。他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敏感問題的熱情關注和獨特思考,對題材、內容和人物的挖掘、處理和表現方面,均有建樹,可圈可點。
在1980年代的上海文壇中,他應該是一位很有創作特點,值得重視的作家。他擅長工業題材的創作,挖掘和講述發生在工廠、企業和機關里的故事,塑造生活在那個天地里的各色人物,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政工干部的形象。他筆下的人物常常會處在一種兩難境地:從個人的主觀良好愿望出發,充滿著工作熱情,卻往往在現實生活中四處碰壁,顯得無可奈何、力不從心,在結尾處理上又透露出一線希望的曙光。充分表現了人物面對現實生活而產生的困惑矛盾心理和被強烈的責任感所喚起的伸張正義、追求真理的內心沖動。其中,或多或少會感覺到有長天的影子,文如其人。
1985年5月,他被選調到上海市作家協會擔任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協助作協黨組書記、主席團常務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茹志鵑老師工作。茹老師長者風范,很信任和支持他,除重要事項由她拍板決定外,作協的日常工作放手交由他主持,給他壓重擔。他與其他三位書記處書記張軍、宗福先和李楚城一起,積極組織開展工作。那年他三十八歲。據說,是上海宣傳系統內最年輕的局級干部。后因工作需要,他向茹老師推薦,調我到作家協會任黨組秘書,那是1985年8月份。此后二十八年共事,他一直是我的領導,文友,但我更認他為我的兄長,他的人格魅力始終感染和溫暖著我。我敬重和佩服他。
當初,航天局是不愿放長天走的,好不容易從基層選拔上來,人才難得,正想培養重用他,卻要被外單位挖走。1980年代的航天局為市里輸送了不少中青年干部,如市委常委、市建設工作黨委書記孫貴璋,市委組織部部長趙啟正,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孫剛等等。如果長天不去作協,留在局里,那么他的仕途前景可能會另一番景象。征求他本人意見,長天選擇了作協。這是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為他太喜歡文學,去作協工作,對他的吸引和挑戰太大了。現在回過頭看,長天當初的選擇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畢竟因他的到來,曾給上海作協帶來青春氣息和清新之風,使上海作協的工作有過一段精彩的記憶。時間也許是最好的見證。
上海作協第四屆主席團是在1984年7月選舉產生的,離上屆換屆大會整整二十二年。因“文革”等歷史原因,造成了正常換屆時間延誤十八年。這屆主席團規模龐大,人數最多,年齡也最大。這是“文革”十年后,撥亂反正的產物。主席團的平均年齡高達六十八歲,但二十位主席團成員都是上海文學界的領軍人物,德高望重、不可或缺。其中,小說家六位:王西彥、師陀、吳強、茹志鵑、哈華、菡子;詩人三位:王辛笛、肖岱、羅洛;劇作家四位:于伶、艾明之、杜宣、柯靈;散文家一位:孫峻青;文藝理論家三位:王元化、徐中玉、蔣孔陽;兒童文學家一位:陳伯吹;外國文學翻譯家兩位:包文棣、草嬰。此外,還有五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團顧問:許杰、朱東潤、伍蠡甫、鐘望陽、趙家璧。作協主席是1930年代初就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的老劇作家于伶。
主席團一年要開好幾次會議,審議和決定一些重要事項。會議的具體籌備工作主要由長天負責組織協調。于伶先生主持會議,話語簡短,盡量請大家多說。茹志鵑老師介紹作協工作情況,提出需要主席團重點研究解決的問題,簡明扼要、言簡意賅,不添油加醋。趙長天列席會議,代表書記處匯報工作,就顯得詳盡細致謹慎多了。記得那時開會討論問題,審議工作,有時大家會各說各的話題,偶爾還會為一個問題爭論得很激烈,甚至還出現過相互拍桌子的場面,難以形成統一的思想和解決問題的意見,結果是議而不決。
盡管如此,工作要繼續開展,任務要盡力完成。作為晚輩,長天還要上門拜訪,耐心說明情況,開展自我批評,做好思想工作,以求諒解和支持。那時的黨組、書記處堅持既開拓進取,又小心謹慎,努力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矛盾,盡心盡力做好團結、聯絡、協調和服務工作,并取得顯著成效。一路走來,確實不易。當然,難免還會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反對的聲音,甚至是責難攻擊。對此,他都能容忍,一笑了之。
一笑之間,他從青年干部變成了老同志,但他的心不老,思想依舊敏銳活躍。他熱情、認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和謙虛謹慎、委曲求全,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胸襟,始終如一,深得人心。現在看來,長天到作協工作,堅守了二十八年,將人生最重要的時間都奉獻給了作協,是時代歷史的一種選擇,偶然中又透出必然,是一種緣。
長天為人處世大度豁達,心胸寬廣悠遠,像他的名字。他柔中有剛,敢于擔當,再難再大再重的事都能自然以對,從容化解。特別是曾經經歷的那場風波,他毅然主動站出來承擔作協的主要責任之舉。記得事后據說有一位領導說了一句話:作家是感情型的,容易沖動,情有可原。言外之意是幫作家們說了一點話。但有人告狀,抓住不放,因此總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他態度很堅決,很坦然,但私下作好了各種準備,甚至坐牢……可見他內心忍受的壓力和痛苦有多大。后來,他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被免去黨組副書記,但保留了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兼秘書長一職,繼續協助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羅洛老師工作。他沒有情緒低落,沒有消極對待,繼續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努力工作。
有時我們私底下聊天,為他抱不平,但是,他總是笑笑說:“算了,讓它去。”要是真能算了,都能放下,也就好了,不至于那么累。記得在2012年初的一天,幾位好友聚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飯局氣氛挺好。長天也喝了一些酒,他不善喝酒,臉有點紅,我坐在他的邊上。大家天南地北地瞎聊,不知聊及了什么,他突然轉臉對我說:“建明,可能因我的原因,影響了你們。” 長天過去叫我小于,記不得什么時候改叫我建明了。他看著我搖搖頭,笑笑,“沒辦法了”。我心頭一緊,鼻子一酸,一時無語,也只能對他笑笑。長天說,算了。可在他的心靈深處究竟還有著哪些無奈的記掛呀?!真能算得了嗎?在1997年作協第七次換屆大會上,他是當選理事中獲得票數最高的一位。算作是別樣一種告慰吧。
長天對自己要求嚴格,不擅長為自己謀取私利。他與人交往,重情重義不重利,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對官場那套阿諛奉承、趨炎附勢的習氣很不以為然。他在官場呆了那么多年,卻沒有學會溜須拍馬、投其所好的“本領”。上級領導到作協來開會、調研、視察工作,他總是實事求是匯報情況,談工作、談問題,不會說好聽的話、討好的話,奉承的話。迎送領導、客人,他會做得很周到,很得體,又很隨意,這是他的為人之道。太過分的熱情舉止他是不會想,不會做的。有一次,一位領導來作協調研,因大家比較熟悉,會開得較為輕松。時間長了,領導內急,起身出來上廁所,就見陪同的一位下屬領導跟了出來,小跑兩步,趕在領導的右前側,微微低頭,舉手引領,守候,又跟著回來。長天看著,微微搖搖頭。后來我們私下當笑料說。他說,這種事我是做不出來的。他是那種很重名節操守,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
長天在作協當領導這么多年,單憑他的創作成就,為他舉辦創作研討活動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事,更不用說近水樓臺了。我作為作協創作聯絡室主任,組織這事也是分內的工作。我曾經向他提過幾次,他都婉言謝絕。1994年,長天在《收獲》雜志第六期發表了長篇小說《不是懺悔》,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了單行本。小說描寫了人到中年的知識分子曲折的人生經歷和困惑、矛盾和復雜的內心情感世界,是一部有特色的好作品。我提議開作品研討會,由創聯室組織,不用他操心,他謝絕了。2003年8月,文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長篇傳記文學《孤獨的外來者——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得》,用作家的眼光和筆觸,真實記述了中國近代史中一位外國人赫得的奇特人生軌跡,社會反響也很大。我又提出過,但他又謝絕了。理由就一條:我是領導,還是算了吧。
他不太為自己的事向人開口,但單位的事、同事朋友的事卻會認真對待,不圖回報。他會充分利用和調動個人的影響力和資源,努力幫助解決問題,甚至開口求人。
1994年,作協成立四十周年,在福州路當時的市府大禮堂舉辦了一場大型慶祝活動,請了不少上海和外地的文藝名家前來慶賀演出。上海電視臺負責演出拍攝和播放任務。可是,預算缺二十多萬。籌備工作在推進,錢還沒落實,大家都很著急。最后還是長天說動了老同學,一位企業老總,慷慨解囊,作為宣傳廣告費一次性得以解決。為了節省開支,有人提議演員出場費分三六九等,大牌的多點。長天很不以為然,他說:“我們都是文藝圈的朋友,應該真誠相待,一視同仁為好。他們不是為了錢,都是沖著作協來的。錢多了拿不出,少了也對不起朋友,每人一千元,作為友情演出的車馬費補貼,要提前講清楚,不要勉強。”最后文藝演出很成功,圈內圈外的反映都很好。
后來,他到《萌芽》雜志社當主編,把主要精力放在《萌芽》雜志的發展和創新上,團結《萌芽》全體同仁,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搞得風生水起,使《萌芽》雜志再創輝煌。為了辦好“《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他通過各種途徑,不厭其煩地找過國家教育部領導,找過上海市委領導和宣傳部領導,找過市教委領導,找過很多國家重點高校的領導,還聯系聘請很多著名專家、學者和作家來出任評委。他還親自到全國各地的有關中學講課,推介此項大賽。
長天骨子里就是個文人,為官多年,文氣未變。他率性坦然優雅、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君子坦蕩蕩。他堅守自己的獨立思想和人格,不會隨波逐流。他平時不太愛說活,不善應酬,更不會溜須拍馬鉆營之術,也不太喜歡那種吹吹捧捧,嘈嘈雜雜的鬧騰場面。他喜靜,看書,喝茶,思考,寫作,上電腦,也練書法,偶爾也會和三五知己眉飛色舞地亂侃神聊一下。他正直誠懇,沒有架子,不會擺譜,待人謙和、友善,善于傾聽。有時候下屬會找他訴苦,請他幫忙辦點事,也不會推脫,耐心傾聽,盡心盡力幫著辦,辦成后輕描淡寫地告訴一聲,就過去了。外出參加活動時,他很會體諒和關心人,拎包、讓座很隨意,別人占了他的座,他就會往后面走,隨便找個座就坐下,沒有半點兒不悅,和他相處很輕松。
作為作協領導,他上下班單位安排車接送。有幾位同事住在他家附近,想搭搭便車。長天說,順便帶帶沒問題。他經常要外出開會、辦事,有時不能按時趕回單位,就會反過來打招呼,不好意思地說明情況。時間長了,同事們也真難為情了,便主動退出了。
長天給人的印象是沉穩、內斂,不喜張揚,其實他內心的情感是浪漫、熱烈、豐富多彩的。這要分場合。比如,長天口才很好,表達力強,開會發言,文學演講,從容不迫,娓娓道來,有思想有觀點,機敏犀利,又實事求是,講到興起時,神采飛揚,妙語連珠。長天偶爾也會在一些聯歡的場合一展歌喉,音色渾厚圓潤,《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等是他的保留曲目,他神情專注,唱得抒情還帶點兒憂郁,略顯拘謹但很投入。
長天為人低調,但不是韜光養晦的權宜之計。他在做人,與人為善、厚道待人,善為自然天性地流露。這是做人的很高境界。不僅如此,他還善解人意。他與人交往或處理事務,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善解別人思想和舉動,細微之處的理解和體恤,分寸感極好。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得理讓人,吃虧即福。這是做人的更高境界。記得我剛到作協工作,作為秘書幫他起草些文件材料是分內的事,可能體諒我初來乍到,情況不熟,也許他習慣了自己動手,內心就覺得應該自己寫。機關的公文寫作與文學創作要求不一樣,是兩種語言、思維和表達系統,好在長天當過多年宣傳干部,對此駕輕就熟。他寫得很快,也寫得很好。有時反過來還讓我看看,幫著修改修改——擔心我會產生邊緣化的不安感覺。后來養成習慣,涉及他自己的工作和想法的有關文字材料,只要有時間,都由他自己親自動手。
長天懂得輕重緩急,懂得平衡兼顧,懂得協調統一,工作從容不迫,應對自如,有著舉重若輕的氣質。我記得,曾任作協黨組書記、主席的老詩人羅洛說過,作協的工作要“無為而治”。長天沒有說,但肯定是認同的。他身體力行地推行和堅守著,不急不躁,順其自然,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不是不作為,而是強調實事求是,抓大放小。抓大,就是要團結和引領廣大作家,努力營造適合社會發展要求,又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和諧寬松的創作環境,圍繞多出優秀人才、多出優秀作品服務。放小,就是對文學創作的具體事盡量少指責,少干預,特別是有違作協性質特點和文學規律的事,少管或不管。作協要去掉官僚衙門之氣,力戒假大空、反對形式主義和虛假浮夸之風,無用功的事要盡量少做不做。這么多年來,作協就是這么腳踏實地走過來的,風清氣正,和諧寬松,尊老愛少,人才輩出。新時期,新氣象,這與歷屆作協黨組、主席團領導的開明大氣、謙和睿智的大家風范有關,與堅持實事求是、開拓進取的精神風貌有關,與薪火相傳、抱團守望有關,也肯定與長天的奉獻有關。
長天走了,離開我們遠行了。記得2012年的春末,長天要到云南去看病。行前的一天,在作協那個經常相遇的樓道里,他從四樓的辦公室下來,正好碰到,我們并肩一塊兒走,聊了幾句。他說要去云南看病。我擔心地問:“你氣色蠻好,沒有什么大問題吧?”他笑笑說:“我也感覺沒什么問題。”他仍然很淡定,樂觀。回來后,他就住進醫院,再也沒出來。一晃快一年了,長天真走了。一直到現在我心里總覺得有點空,有時候坐立不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在作協大院里久了,年紀也大了,我感覺到了時間的飛逝。一個時代正在逝去,當年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的一代青年,已與那個年代漸行漸遠。恍惚間,已物是人非。留下更多的便是回憶。人已遠逝,這個大廳,和廳外的風景,依舊,但我相信人的靈魂和精神是不滅的。長天還活著,他的氣息還在上海市作家協會這個大廳里,我感覺到了。
原文發表于《上海文學》201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