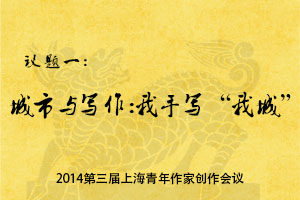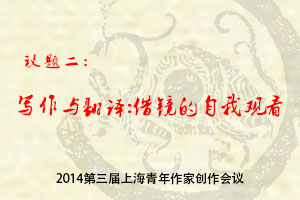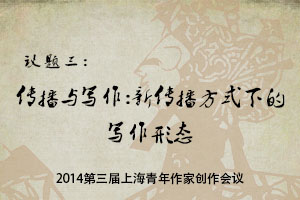這幾天,亞信峰會正在中國舉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個(gè)國際化大都市的風(fēng)范。隨意行走,人們已經(jīng)很難區(qū)分這里與紐約、倫敦的區(qū)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在都市里成長的一代人對這種變化更有切膚之感,分享城市化帶來的進(jìn)步,也必須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們寫下的關(guān)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誘惑與抗拒并存的態(tài)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的創(chuàng)作從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產(chǎn)生焦慮和困惑,其經(jīng)驗(yàn)具有普遍性意義。
在不久前召開的第三屆上海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會議上,有許多已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翻譯家和評論家與會,如周嘉寧、小白、路內(nèi)、蔡駿、甫躍輝、黃昱寧……他們不只屬于"文學(xué)圈",在圖書市場上也很受歡迎,尤其受青年讀者的青睞。這大概因?yàn)樗麄兊膶懽饕曇皬V闊,筆下的都市經(jīng)驗(yàn)更能引起共鳴。記得當(dāng)時(shí)有人開玩笑說,"以后中國寫城市就看你們的了",這話當(dāng)然有戲謔,想想也不無道理。破解城市文學(xué)之困,真的要看這一代作家的表現(xiàn)了。
一個(gè)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
查閱這些青年作家的履歷,會發(fā)現(xiàn)一個(gè)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一邊寫小說,一邊翻譯別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變成了譯者。出版短篇小說集《迷走·神經(jīng)》的BTR,同時(shí)翻譯了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孤獨(dú)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周嘉寧除了寫小說,還翻譯了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寫在身體上》和米蘭達(dá)·裘麗的小說《沒有人比你更屬于這里》。胡桑除創(chuàng)作詩集《賦形者》等,還翻譯了辛波斯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等。寫《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時(shí)也出版了《窮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譯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幾種外語,他在發(fā)言中從"小說"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中的詞根講起,談到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小說傳統(tǒng)。
這么多的作家,既能寫小說,又能翻譯小說,他們可以站在"世界"上寫作,這的確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現(xiàn)象。所以,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李敬澤說,"他們是一個(gè)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并相信"他們能為都市經(jīng)驗(yàn)的表現(xiàn)提供很多創(chuàng)新因素"。李敬澤說,上海一直以來都是一個(gè)面向世界、面向現(xiàn)代、面向未來的城市,它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來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們對城市、國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覺的認(rèn)識。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語、視野開闊、感覺敏銳,這是在上海寫作的獨(dú)特優(yōu)勢。他們能為都市經(jīng)驗(yàn)的表達(dá)尋求新的可能,能為中國文學(xué)帶來創(chuàng)新元素。
既是作家又是譯者,翻譯別人的作品同時(shí)會影響自己的創(chuàng)作。BTR以自己的經(jīng)驗(yàn)講述了翻譯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認(rèn)為,翻譯是很好的語言練習(xí),譯者要費(fèi)心思找到恰當(dāng)?shù)膶?yīng)的詞語和句子,還得細(xì)讀原著,掌握它的語言風(fēng)格。原著的風(fēng)格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譯者的創(chuàng)作,比如節(jié)奏的掌握、語感的契合。但在翻譯和寫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國作家莉迪婭·戴維斯翻譯普魯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寫小說時(shí)就不會寫普魯斯特式的長句子,而更偏愛短句子。
黃昱寧更多時(shí)候是在做翻譯,也寫隨筆,目前她已經(jīng)翻譯了近10部作品。她說,"將原文轉(zhuǎn)化為中文的過程,既不斷刺激我在創(chuàng)作中的表達(dá)欲,有時(shí)候也會抑制我的表達(dá)欲,這兩種互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個(gè)更強(qiáng)大,還是勢均力敵,這常常構(gòu)成困擾我的問題,因?yàn)楹玫奈谋窘佑|太多以后,我會覺得寫下什么都是錯"。脫離開自己的寫作,她認(rèn)為翻譯文學(xué)應(yīng)該比原創(chuàng)文學(xué)"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創(chuàng)文學(xué)的發(fā)展。
作為譯者,他們把世界文學(xué)帶給讀者;身為作者,他們?nèi)诨@些資源,寫下自己的作品。評論家木葉說,創(chuàng)作本身是一個(gè)人的事兒,你所喜歡的大師和經(jīng)典文本都無法替代你的哀愁、瘋狂與痛苦。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翻譯。"一個(gè)優(yōu)秀的作家,最好能夠把自己的時(shí)代翻譯出來,把內(nèi)心那些幽微的聲音翻譯出來,再簡單一點(diǎn)就是把自己的高尚與齷齪、勇敢與懦弱都翻譯出來。"
變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誰
一說寫城市,就難免要拿鄉(xiāng)村作參照,一比就顯出了城市文學(xué)的弱勢。說到底,是因?yàn)橹袊诤荛L時(shí)間里都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們類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在這個(gè)問題,但是他們在寫都市的過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麻煩。幾乎每一天,城市都在變化,迅速到讓人無從把握。面對高大的要失去界線的城市,看不見自己,找不到故鄉(xiāng)。
生在上海也去過其他城市的周嘉寧,把空間分為"城市"和"非城市",因?yàn)樵谒磥碇袊某鞘袔缀跏且粯拥模鼈儾鹆擞纸ǎ絹碓较嗨啤3鞘薪⑵鹜暾捏w系和規(guī)范的標(biāo)準(zhǔn),這讓她陷入寫作的焦慮:一切都太符合規(guī)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太相似了。這讓寫作喪失了生命力,寫作本身也變得規(guī)矩起來,這時(shí)候她反而羨慕那些在鄉(xiāng)鎮(zhèn)生活的人們,渴望那里驚心動魄的故事。
"城市讓我眼花繚亂,當(dāng)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時(shí)候,我覺得如同盲人摸象"。盡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覺得,自己無法概括一座城市。變化太快,人們擁有太多渠道了解超負(fù)荷的信息,最后每個(gè)人選擇自己認(rèn)可的捷徑,孤獨(dú)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鳴的話,更多也是對孤獨(dú)的共鳴。
這種感覺在作家甫躍輝的小說《巨象》里也有表達(dá),主人公李生一次次夢見巨象的身軀、腳掌、呼吸,越來越頻繁。評論家黃平用這個(gè)意像來解讀作家與城市的關(guān)系。他認(rèn)為,作為城市的外來者,郭敬明們用消費(fèi)主義的邏輯消解了與城市的緊張感,而甫躍輝們則選擇以這種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學(xué)書寫需要的是社會史的寫法,年輕的寫作者應(yīng)該思考,能不能寫出更大的意義。
評論家金理談到,現(xiàn)在青年人的寫作需要爆發(fā)一種精神力量。這就像評論家吳亮說的,"現(xiàn)在的文學(xué)批評需要荷爾蒙",其實(shí),文學(xué)創(chuàng)作同樣如此。金理說,上世紀(jì)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變城市的意愿,而現(xiàn)在這種力量似乎弱化了,變得暮氣沉沉。或許,只有在青年人可以正視他的自由、欲求、情緒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時(shí)候,才會誕生真正的青春文學(xué)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學(xué)。
在作家王若虛的眼里,城市寫作的重點(diǎn)應(yīng)該是城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異,個(gè)人、階層、群體的差異。他想寫一部小說來表現(xiàn)這種差異,他曾發(fā)現(xiàn)在一所初中里,本地學(xué)生和外來務(wù)工人員的子女被區(qū)分對待,老師甚至不允許他們在一起玩兒。這就是城市內(nèi)部巨大的差異性,人與人之間常有各種各樣的機(jī)會產(chǎn)生微妙的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里存在著城市的生活價(jià)值與生活意義。
城市生活的價(jià)值和意義是什么?這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題目。隨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加快,數(shù)目眾多的中國人進(jìn)入城市并開始在城市里生活,這種新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學(xué)的記錄和表達(dá),尤其"城中人"的狀態(tài)更需要關(guān)注和書寫。無論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shí)來看,上海都可以被視為中國城市發(fā)展的一個(gè)樣本,因此,探討上海城市文學(xué)的書寫經(jīng)驗(yàn),會為更大范圍內(nèi)的城市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來啟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們在書寫城市的過程中體現(xiàn)出了優(yōu)勢,有自己的城市坐標(biāo),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們能把這種優(yōu)勢同對"吾土吾民"的認(rèn)知和情感融為一體,相信城市文學(xué)的突破,必將有賴于這一代人的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