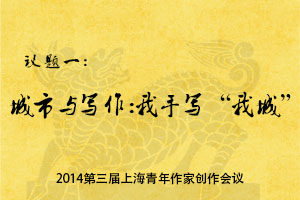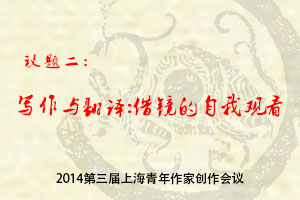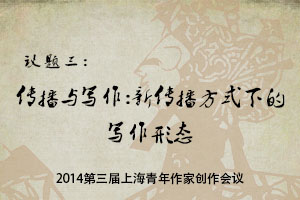青年作家于是:
翻譯是我近年來(lái)的一件主要工作。一開(kāi)始只是從兒童文學(xué)入手,逐漸進(jìn)入類(lèi)型文學(xué),繼而產(chǎn)生了"想翻譯自己喜歡并欣賞的作家作品"的主觀意愿。類(lèi)型文學(xué)是很有養(yǎng)分的,我翻譯了三部斯蒂芬·金的作品,對(duì)他的風(fēng)格已是了然于心。繼而翻譯了溫特森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這本書(shū)在青年讀者中的影響特別大,我不認(rèn)為這是譯者的功勞,完全是作者本人的魅力使然,她自由的文風(fēng),誠(chéng)摯的訴求,大膽的改編經(jīng)典甚至《圣經(jīng)》……都是文學(xué)史上不可多得的天才之舉,對(duì)于大多數(shù)以書(shū)寫(xiě)自我起步的作者來(lái)說(shuō),她的這種坦然和率性能夠針砭到我們自身對(duì)"個(gè)體性"的狹隘態(tài)度,從而將個(gè)體寫(xiě)作帶上更高的層次。
青年作家小白:
通過(guò)翻譯重新構(gòu)建小說(shuō)傳統(tǒng):1、漢語(yǔ)所謂"小說(shuō)"和西語(yǔ)中的對(duì)譯詞所指到底是不是一回事?2、對(duì)寫(xiě)作者來(lái)說(shuō)何謂"小說(shuō)的傳統(tǒng)"?3、中國(guó)小說(shuō)的"道路自信"在哪?
青年作家BTR:
1、寫(xiě)作是一種廣義的翻譯:(1)翻譯想法,口語(yǔ)到書(shū)面語(yǔ)的翻譯,方言到普通話的翻譯;(2)翻譯已知的事實(shí)——如自傳體寫(xiě)作;(3)符號(hào)學(xué)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之間的互譯;(4)對(duì)應(yīng)地,閱讀或理解過(guò)程也是一種翻譯過(guò)程;
2、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1)對(duì)比法語(yǔ)、西語(yǔ)-> 英語(yǔ)等同一系統(tǒng)下的翻譯,翻譯成中文需要再創(chuàng)作;(2)翻譯是了解作者的觀念,再以本國(guó)語(yǔ)言表達(dá)。
3、作者/譯者的雙重身份之利弊:(1)翻譯是很好的語(yǔ)言練習(xí);(2)譯者風(fēng)格與所翻譯的作者風(fēng)格的契合;(3)對(duì)于作者風(fēng)格的正反影響;(4)對(duì)于語(yǔ)言本身的影響
青年作家黃昱寧:
翻譯文學(xué)是近代以來(lái)深入改變中國(guó)文學(xué)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力量,這種影響隨著全球化的到來(lái),在今時(shí)今日正向更縱深處發(fā)展。這種影響往往被低估或者曲解,或者流于表面(更多被提及的還是語(yǔ)言上的流變,程式上的借鑒,而非文學(xué)視野和思維方式上的滲透),文學(xué)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寫(xiě)作"的位置,其在理論上的認(rèn)定仍落后于實(shí)踐。現(xiàn)代中文寫(xiě)作及現(xiàn)代中文對(duì)"翻譯體"和世界文學(xué)潮流的逐漸吸收和接納,反過(guò)來(lái)也對(duì)翻譯文學(xué)的價(jià)值和標(biāo)準(zhǔn),提出了新的要求。 介于翻譯與寫(xiě)作之間或兩者兼?zhèn)涞淖g者/作家,是對(duì)上述互動(dòng)和碰撞關(guān)系最敏感的人群,構(gòu)成一個(gè)獨(dú)特的文化現(xiàn)象。在世界范圍內(nèi),最著名的兩個(gè)例子是村上春樹(shù)和納博科夫。
青年作家俞冰夏:
我個(gè)人從事文學(xué)翻譯有一定年數(shù),一直被中國(guó)出版商對(duì)譯注的重視所迷惑。譯注的傳統(tǒng)可能來(lái)自于國(guó)內(nèi)語(yǔ)文教學(xué)的傳統(tǒng)也可能來(lái)自早期外國(guó)文學(xué)"譯介"傳統(tǒng),它的前提是國(guó)內(nèi)讀者對(duì)源語(yǔ)言國(guó)家文化的認(rèn)知程度為零或基本為零。譯注在文學(xué)翻譯當(dāng)中的具體體現(xiàn)是一種第三方認(rèn)識(shí)論(譯者或編輯的個(gè)人認(rèn)識(shí)論)的插入,對(duì)文本無(wú)疑是種外部介入和再闡釋?zhuān)瑫r(shí)無(wú)意識(shí)阻擋了讀者有可能進(jìn)行的外伸性閱讀。趁此機(jī)會(huì)希望能進(jìn)行一些探討。
青年作家胡桑:
每個(gè)時(shí)代對(duì)語(yǔ)言的運(yùn)用和理解都在變化,語(yǔ)言是流動(dòng)的,翻譯捕捉到了這種流動(dòng)的痕跡。隨著時(shí)間的展開(kāi),我們不斷地需要翻譯。翻譯不僅是共時(shí)的交流,也是當(dāng)下與過(guò)去的交流。翻譯不是搬運(yùn),而是在另一門(mén)語(yǔ)言中找到合適的形式。另一方面,這種合適的形式并不意味著最符合漢語(yǔ)的表達(dá)習(xí)慣,有時(shí)候盡量保留原語(yǔ)言別致的表達(dá)方式可能為為漢語(yǔ)帶來(lái)陌生的令人驚喜的東西,這是翻譯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也是翻譯忠誠(chéng)于原語(yǔ)言帶來(lái)的收獲,盡管這收獲必定來(lái)得艱難。翻譯與寫(xiě)作是一個(gè)互相激勵(lì)的過(guò)程。真正的寫(xiě)作狀態(tài)就是翻譯的狀態(tài)。它不斷向陌生的、他者的、差異的世界開(kāi)放、吸納并自我提煉。翻譯就是渴望開(kāi)拓自己,就是渴望交流,渴望獲得對(duì)世界的不同理解。
青年評(píng)論家薛羽:
"翻譯"與"書(shū)寫(xiě)"之間的文學(xué)者——以魯迅為例,"閱讀"始終處于"交叉"的網(wǎng)絡(luò)之間,既和"閱讀者"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性"有關(guān),也與他所處時(shí)代的語(yǔ)境深刻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作為"作者"的魯迅誕生之前,一個(gè)作為"讀者"的魯迅則已經(jīng)進(jìn)行了多年的閱讀和翻譯實(shí)踐,而為數(shù)眾多的研究也已經(jīng)證明,魯迅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背后有著多少的"露西亞之影";若是依據(jù)更為開(kāi)放的理解,把早期的論文、譯作都視為魯迅的"創(chuàng)作",那么也不能不說(shuō)作為"作者"的魯迅甫一開(kāi)始就是與作為"讀者"的魯迅密切聯(lián)系,相互生成與展開(kāi)的。
青年評(píng)論家張定浩:
我們都知道美國(guó)詩(shī)人弗羅斯特有句話,詩(shī)就是在翻譯中遺漏的東西。但其實(shí),還有一直存在另外一種相對(duì)應(yīng)的說(shuō)法,那就是歌德所說(shuō)的,"詩(shī)歌的根本性質(zhì)在于能夠被翻譯成另一種語(yǔ)言。"所謂詩(shī)言志,詩(shī)歌最終是要表達(dá)人心里面的感受。我們知道,不同種族,不同性質(zhì)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huì),會(huì)造就不同的人,人們會(huì)在哲學(xué)層面吵架,在倫理層面吵架,會(huì)充滿(mǎn)各種各樣無(wú)法調(diào)和也無(wú)法相互理解的爭(zhēng)執(zhí),然而,在美的面前,以及在巨大的痛苦面前,我覺(jué)得,再千差萬(wàn)別的人,都可以相互交流。
青年評(píng)論家黃德海:
在譯者認(rèn)真的前提下,我認(rèn)為,談?wù)摲g的優(yōu)劣不少時(shí)候是荒唐的。何況,即使譯本本身優(yōu)劣分明,是否那個(gè)優(yōu)的譯本就一定在漢語(yǔ)語(yǔ)境中勝出,還在未知之?dāng)?shù)。
既然翻譯的優(yōu)劣不那么容易判斷,那么,好的翻譯要滿(mǎn)足什么條件呢?好的翻譯大概是這樣一種境界,譯者反復(fù)細(xì)致地閱讀原本,最終透徹地理解了作者的意圖,然后用另外一種成熟的語(yǔ)言把這個(gè)意圖還原出來(lái)。這樣的翻譯出現(xiàn),一個(gè)譯本才能真正在另外一個(gè)語(yǔ)境中落地生根,那些異質(zhì)的思想和價(jià)值體系,才能與本土的思想和價(jià)值體系對(duì)峙、交鋒、融合,從而呈現(xiàn)出各自最為精妙的部分。而這些翻譯文本,也才能最終成為漢語(yǔ)的一部分,像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jīng),參與一個(gè)活生生的思想和語(yǔ)言成長(zhǎng)過(guò)程。
青年評(píng)論家木葉:
翻譯與寫(xiě)作,先從古代講起,再說(shuō)近代,例證很多,到了全球化的時(shí)代,翻譯和寫(xiě)作一直是相輔相成的。有偉大的寫(xiě)作的時(shí)代,往往是有偉大翻譯的時(shí)代。作家自身就是翻譯家,即便不是,作家自身也在翻譯文本的氛圍之中。翻譯文本也成為一種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