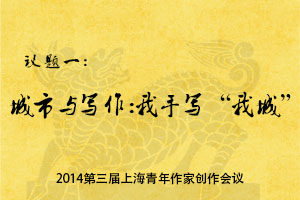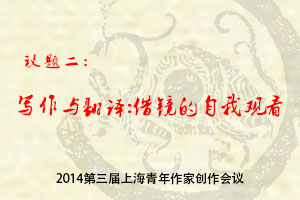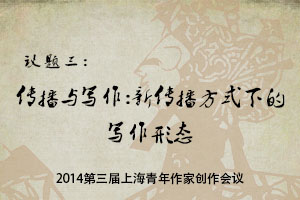白燁(著名評論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發言:
參加上海青創會收獲很大。
上海青年作家隊伍的實力、活力在今天得到最好的證明,上海和很多省不太一樣的地方在于,很多省市50、60后作家很多,70后作家還可以,80、90后作家就非常稀少。而上海是70后、80后、90后隊伍非常雄壯。這就預示著上海文學發展的前景和后勁,過三五年就可以看出效果,這是非常好的財富。什么是文學的財富?就是人才,有這么多文學作家聚集在一起。我參加過西安的青年作家會,他們是中青年作家一個班,幾乎沒有80后作家,都是以60后和70后為主,我認為這不行,必須要有80后作家,畢竟現在90后作家都開始出現了。在其他省找80后作者就很困難,但是現在我們這里有很多,這筆財富對上海而言是非常寶貴的,是別的地方不能比的財富。

今天聽了大家的發言很受啟發,從每個人發言中能夠看出他的想法。這是一個結合了個人創作、個人視角的想法;同時也有個人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和他所置身這個城市的特點。所以我對上海文學今后的發展抱有很大的期待,有時候文化的發展需要靠創作和批評兩輪的驅動和互動的,上海擁有這樣一群80后批評家是非常難得的。
當然也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現在80后的批評家對同代人的關注還是不夠的,就是他們的興趣點、知識結構來看,更多的接近于父輩、長輩、老師輩。我覺得更應該體現出他們的特點,同時又要針對他們所面對的,去好好解讀同代人的創作。因為在我看來80后的創作,不僅僅是80后寫作本身,其實還是這個時代演變的最好的樣本,這個時代在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通過80后的寫作,可以看出一代人寫法、姿態、觀念的不同,同時他們能受歡迎,說明他們的讀者群是一樣的,也表現了這代人整體是另一種觀念和趣味,再跟我們相區別。現在的文學和過去最大的區別是,過去文學相對單純,現在的文學越來越混敘。我覺得80后、90后對這個時代能作出非常好的解讀。
總體來看,上海無論在創作還是研究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資源和對象。可以說80后棋手級的作家在上海,而70后寫作的主將也在上海,并且在座的還有90后作家。今天再次證明上海的青年作家真是前途無量。
我跟蹤80后作家,一開始是不自覺的,從不自覺到自覺有十多年了, 98年我做了一本書,是許佳的《我愛陽光》,這個孩子當時是上海的中學生,他在中學生時期寫完了這個作品,98年出版。之后我們在北京見過面,他用一種很不屑的口氣,不知他從哪來的對我們這些人--他的父輩有很多不滿,他說你們那些人很虛假,把極左和政治連在一起,你們怎么對政治那么感興趣,我感到不能理解。我聽后很震驚,后來跟他解釋,我說你不了解,那時候熱衷于政治,對我們而言也是不虛假的;我說那時候我們為了表現好要入黨,找好人好事找不到,就想把誰推下河去,然后拉上來,到山上放一把火,然后自己再滅火。當時這個孩子的作品和與他的對話,給我很大的刺激,他們這代人有自己的看法,對于政治這樣東西是排斥的。
03年的時候,北京開了一個青年文學座談會,我在那個會議上第一次看見郭敬明,第一次看的時候還不敢認,因為頭發很長,手上戴個戒指,在我旁邊,從那之后開始和他認識,同他也吃了一次飯。06年,我在網上有一篇文章,叫做《80后現狀和未來》,被韓寒看見,后來發了一篇駁文《文壇是個屁》。后來我思考,這幾次跟文學或者跟80后作家的接觸是有一種神秘的勾連,也可以看出在這過程中是既受累,也受惠,通過這樣的接觸使我們更好的,因為我們原來總認為年輕人是需要引導的,我們總是比你們成熟,后來受到了刺激以后,思想開始改變。一開始我認為你們那個不叫文學,當時有一句話:你們走上了市場,沒有走上文壇,別以為出了兩本書,賣得不錯,就以為是作家了,我認為這個作家有門檻,有指標的。
現在我的看法是,不能說它不是文學,它可能不是我們傳統的文學,或者不是嚴肅意義上的文學,可能是市場化的,或者青春化的,但是它也是文學。用今天的觀點看,可能不是好的文學。這幾年在和他們接觸中,一開始會與80后作家接觸得多,之后會更多的了解他們。對傳統不理解的80后,我很著急。比如我有一個哥們說,80后那些小屁孩,你成天替他們說話有什么意義,我覺得不是,還是不要小看他們,因為他們作為一代人畢竟是要上來的,他們必定會帶著這一代的特色。在接觸過程中,確實感到他們有屬于他們的銳氣和才氣,但是確實也有他們的問題。同很多專家聊的時候,發現他們幾乎沒有對當代文學的閱讀積累,我經常問一些作家,我說你喜歡哪些當代作家?好幾次,他們就說當代還有我值得看的作品嗎?就是非常不屑的回答。
剛才永新說他們想要80后的作品上文章。有一個雜志約我,說今年第一期開始,為他們做一個80后的專欄,我先后約了十個人,作品來了以后沒有一篇能夠選上,就用我的標準看,哪怕把我的尺度放寬也選不上,我覺得他們在語言到編制故事能力上確實不行。
我現在再想,他們確實有自己的長處,但短處也很明顯。我認為80后通過閱讀,包括更加注重個人的人生體驗,而不是把創作主要建立在書本知識基礎上,在我看來這對于80后來說非常重要。一代人都有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留下的自己的經典作品,現在80后的可以稱之為經典的作品,我覺得很難找到或者幾乎很少或者沒有,這是非常嚴峻的問題。
80后總體狀態是很分化的。有一次我到天津,當時我說希望你們靠近傳統,不要過于游戲,突然有一個90后站起來說:我游戲文學犯法嗎?我對文學就這么看,我就愿意這么游戲,難道不可以嗎?當時我們就楞住了,因為那個觀念和我們完全不同,無法跟他對話下去。我是覺得一定要在和別人的接觸中、碰撞中相互取長補短。可能我們對于商業性、游戲性有一些排拒,80后對這個就比較駕輕就熟,容易接納。但還是要考慮,我們管理文學經驗的看法和期望有沒有合理性,從長遠看有沒有可以繼續的一些地方。我覺得就要通過這種交流、碰撞來相互改變。現在我們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確實在文學里面持不同觀點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時候要有一種多元環境、多元共存的態度,但是在這里我們確實還存在著怎樣互相啟發和促進不斷改變的問題。
上海有這么多作家,作協也很重視。我希望把作家個人的很好的素質、造詣變成寫作,變成群體性,變成上海文學,每個人都很好,但是整體上看合力不夠,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上海還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